發布日期:2017-02-07更新日期:2017-02-07
【名家專欄】
來自某一時刻
我回到甘蔗田裡,甘蔗仍然在風中搖晃生長,譁譁簌簌,看不見盡頭。我摸摸新長的甘蔗葉,沒有一點啃食過的樣子。老鼠變少了,是不是有蛇出沒呢?
祖父母過世後,我很久沒來這片甘蔗田了。
事實上不只我,誰都不來了。小時候這裡曾是我們的球場,只在特定時刻存在的球場,像是有著自己的球季一樣。每到甘蔗收成後重新翻土的冬天,村裡的小孩呼喝著拎了木棍和球從巷弄裡跑出來,連最遠的小鎮也有人騎著腳踏車來看熱鬧。鬧哄哄的比賽太歡樂了,打者手中通常不是正規的球棒,什麼棍子都有,通常和等等回家要挨爸媽揍時是同一隻。球則比較可以想像,有時是紅線球,有時是壘球,有時是軟軟的像熟成的水果一樣的網球,不知都是打哪弄來的。真到山窮水盡時,也總會有人從學校找來躲避球或足球,放下棒子改踢足壘。日曬雨淋,迎風奔跑在起伏的土堆間,滿身泥濘,有一種一起跋山涉水經歷好多事情的況味。
蛇,或鼠,有時會干擾比賽。球打擊出去所有人都動起來,忽然有人哎呀一聲跑離用小石子排出的壘線外,或是本來追著球突然緊急剎車往回跑,大概就是了。突然竄出的老鼠,或蛇,嚇壞了比較少下田幫忙的小孩,突然以一種非常現實、強迫所有人出戲的方式打斷了比賽。棒球比賽就此暫停了,瞬間升級成圍獵活動,所有人都跑下場,在巨大的田地上翻查尋找,一直到太陽下山為止。
通常什麼都找不到。但一切都改變了,活動很快進入另外一種氛圍,農家的小孩取得了全部的指揮權,帶著大家仔細搜索一個又一個……該稱為洞穴嗎?有些洞口堆著疏鬆的黃土,有些沒有,有些洞口與小孩的拳頭大小差不多,有些只比手指稍粗一點,有些黑黝黝的向下延伸看不見底,有些則似乎與地面平行……。各種特徵的洞都有各自的名堂,有些屬於蟋蟀,有些屬於螞蟻,有些屬於蛙和蟾蜍,有些應是老鼠的,有些則是蛇的。但誰知道呢?我們這些比較缺乏實戰經驗的,有時會站在一旁議論紛紛:鼠是蛇的食物,若是鼠躲在洞中,那裏頭就不可能有蛇。但若裡頭有鼠,蛇又怎麼可能放過?蛇不放過的話,田鼠當然就不敢躲在洞裡了。然而再退一萬步說,如果所有的洞裡都沒有老鼠,蛇又如何願意待在沒有食物的田地的洞中呢……
這樣的討論毫無意義,但真有趣,彌補了我們無法參與時空洞的心情。其實也不需要知道太多,不能發號施令的時候,知識是無用的,有用的是膽子。誰敢去提了水站在第一線把水往洞裡灌,誰敢去洞後拎著鏟子往下鏟把動物逼出來,誰敢拿網子負責抓洞裡竄出來的──理論上是什麼但其實沒人有把握的動物呢?
害怕的小孩,往往找了藉口躲在後頭。和其他沒爭取到工作的孩子一樣,站在風呼呼吹著的田埂上圍事把風。「好討厭啊,干擾我們打球」,有時會有人這麼說,蹲下來拔著雜草或小花,出於各種不同的情緒和理由。有時是懊惱不甘,有時是落寞,有時是故作輕鬆但恐懼的,有時只是想找話說……
但事實上,是我們的球賽干擾了動物們的生活才是啊。我不知道別的小孩怎麼想,一定也有人是這樣想的吧?事實就是這樣啊。
每年總有新來的小孩不知道這是怎樣的事情。但反覆幾次,誰都知道洞裡可能躲著動物的事。這樣的情緒後來也會慢慢影響比賽,有時候,有人會說,賽前先清個場吧,大家七手八腳花了幾小時巡遍比賽的場地,一堆人靠在洞口附近,拉了網和棍子,各個洞口同步守著,大桶的水備好了就要往洞裡灌,完全沒有圍師必闕的意思。有人拉了家裡的狗狗過來幫忙,狗狗很高興的奔跑在田間,東聞聞西嗅嗅,毛色在夕陽裡漾著淡淡的金光,好像被寄託了很多很多的希望。
有時懷疑和恐懼,就只是懷疑和恐懼。比賽照常進行,讓人害怕、卻無人敢承認的不明的洞穴就在那裡,守備時不敢太靠近,跑壘也要繞過那裡,球往那一帶滾時所有人都心裡一驚。生怕驚動了什麼我們不想看見的東西。
但就是不會有人承認。故作鎮定多年,長大的小孩各有各的理由在意自己的面子。有人就不再來球場了,有人來了也不比賽。再更多年過去,故作鎮定變成了故作多情,多數人陸續搬離這裡,其中只剩下很少的人──比如說我,記得棒球比賽的事情。留下來的人幾乎都不記得了,就算記得也不在乎。收成完以後,是批貨和處理收成的忙碌的季節了。
「甘蔗田」一直在那裡。後來聽說也不一定種甘蔗了。
還好這次回來,仍是甘蔗的季節。我站在田邊,胡亂想著這些與那些,不知為何又記起了這樣的畫面:比賽結束的時候,一起打球的夥伴們紛紛走出甘蔗田,各自要回家了。我邊走邊回頭,看見大多數的同學朝著夕陽的方向走,模模糊糊的背影,總覺得有點浪漫的感覺,但又有隱隱的不捨和恐懼。這是我們的甘蔗田,明天、後天、大後天、明年的這個時候,我們一定要再在甘蔗田裡相見。我們會再在甘蔗田裡相見嗎?
多年不見的甘蔗田裡,遠遠的有一個陌生的老先生從田埂上走回來。其實應該是村裡認識的長輩,但我已經認不出他了。他走著走著,停在引水的溝渠旁,彎下身,伸手查看一個小小的土洞,然後站起來拍掉手上的土屑,轉身往隔壁的田地走去。
好多事情都改變了。我走過去,在田埂上蹲下來,隔著一小段距離望著那個洞,默默想像,蛇蜷曲著還原為一個小小圓圓的點,黑黑的,不聲張,像是一個洞,又像是一隻老鼠,蹲坐在那裡嗅聞氣味的樣子。

◎林達陽
高雄人。高雄中學畢業,輔大法律學士,國立東華大學藝術碩士。 在離海不遠的地方長大,喜歡書店、電影院、室外球場。著迷於旅行、日常巷弄和能夠看得很遠的地方。曾獲三大報文學獎、台北文學獎、香港青年文學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優秀青年詩人獎等。詩集:《虛構的海》、《誤點的紙飛機》;散文:《慢情書》、《恆溫行李》、《再說一個秘密》、《青春瑣事之樹》。
FB:「林達陽」
Instagram:「poemlin0511」
天荒地老之牆
〈傾城之戀〉裡著名的場景──一堵灰牆,反襯出白流蘇的血肉感,彷彿她是個真情實意的女人,於是范柳原說:「這堵牆,不知為什麼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類的話。有一天,我們的文明整個的毁掉了,什麼都完了,燒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許還剩下這堵墙。流蘇,如果我們那時候在這牆根下遇見了。流蘇,也許你會對我有一點真心,也許我會對你有一點真心。」
牆是這轟隆變動的世界的基底,是試探的邊界。那灰色與粗礪,反試煉出情感裡的一點血氣。流蘇與柳原雖是各懷鬼胎,畢竟是在大時代煙花底下,自有一份反諷的華麗;也曾有那麼一堵灰牆襯在我的生命裡,但那是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中學女生日常,與浪漫與反浪漫都牽不上關係。
放學時七十五路公車慢吞吞開在中山路上,右手邊長長一堵灰牆,圍起中山路與凱旋路口一大塊地。是兵工廠,正式名稱「國防部軍備局生產製造中心第205廠」。日日行過,卻從來不知道那裏頭的模樣,唯一一次有機會進去,還是已成末代絕響的軍訓課打靶練習(烈日下瞇起眼我想知道打靶成果,但靶上坑坑洞洞根本搞不清楚,也可能每一發都奉獻給虛空了),借用廠內的靶場。如果是騎腳踏車回家,一樣經過此地,牆上哨亭漆成灰綠,裏頭站著人,苦悶到想拆牆的阿兵哥們,一看到白衣黑裙女學生騎車過去,絕不放過機會,必然遠遠探頭就大喊:「學妹!」如果不理,還會持續喊話,動之以情:「學妹學妹,看看我嘛,我們聊聊天嘛。」在那樣彆扭的年紀,誰會停下來跟陌生男人說話呢,加速通過後就聽見阿兵哥後頭哈哈哈響亮乾笑追來;有次學長騎機車載我回家,途經兵工廠,剛好一軍用卡車正要開進去,略停在門口,後斗密密填了十幾個兵,大夥一齊盯著我們,拉開喉嚨:「談戀愛哦!報告教官哦!」
對,那個時代,教官就是管學生談戀愛的。學校裡還管頭髮長度與鞋襪顏色,不是太嚴格。朝會早晨,頭髮過長的女孩子們紛紛把馬尾梳高,再結成辮子,能有效在形式上減少長度,教官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算了。解嚴才剛幾年,印象中校園裡沒什麼嚴重思想問題值得被管理,只有永恆的戀愛,蠢蠢欲動的賀爾蒙,流彈也似在巴不得能進行除菌消毒的校園內造成隱憂。校園以牆與外界區隔,校園內也還起伏著各式各樣的牆。前陣子回高中母校一看,外牆也沒了,公園化,以流動取代隔絕。
兵工廠那堵灰牆還在,長長遠遠蜿蜒著像異世界邊線,哨亭裡沒有人了,外邊公佈欄裡的告示不知道是幾百年前的,都脆黃了。然而,這座廠其實也要遷離此地到大樹去,從門口的蕭條來看,也許裏頭已經逐漸搬空,牆是最後才會拆去。沒有哪一堵牆是真正天荒地老。只有中山路還是一樣寬敞到像河道,過江之鯽啊我也是其中一尾,所有機車汽車來了都卯足了勁,彷彿什麼無形的波浪推動著,望不到盡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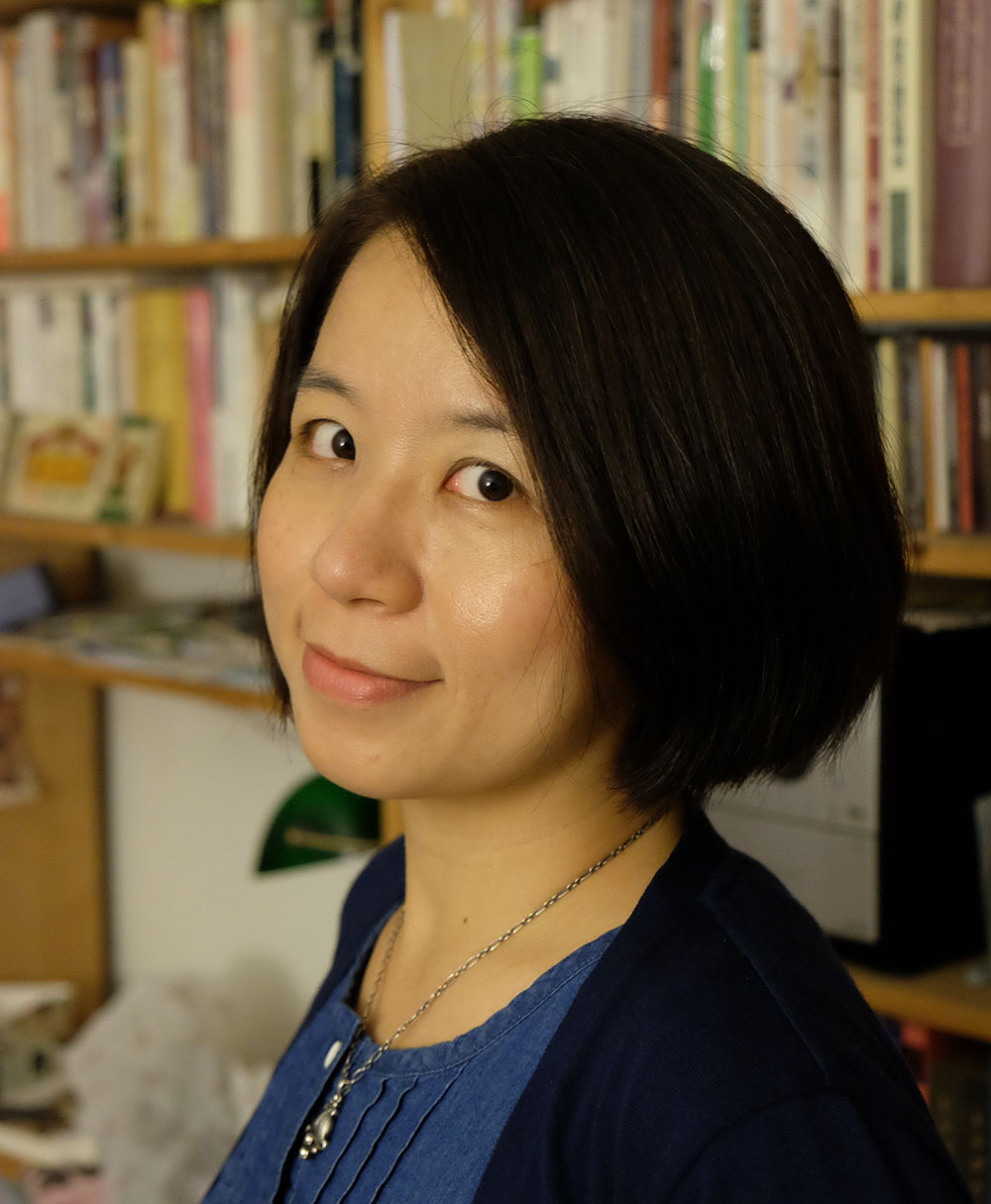
◎楊佳嫻
台灣大學中文所博士,清華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著有詩集《屏息的文明》、《你的聲音充滿時間》、《少女維特》、《金烏》,散文集《海風野火花》、《雲和》、《瑪德蓮》。
蓮池潭的兩隻寄居蟹
「要去看寄居蟹!」這句話總是在我爸說要去龍虎塔之前說出來。
在我小的時候,爸爸只要有機會就會帶我去蓮池潭走走,當然最重要的就是要去龍虎塔裡嘍!或許我爸爸怕我學壞吧?他總是帶我去那玩,並且一一講解著龍身裡牆壁上不同的故事,要怎麼做人以及各種生活常規,還有一大堆早就不知道重覆聽過幾百次的舉例、叮嚀,故事講完了,就輪到講我最喜歡但也最討厭的18層地獄,父親開始述說如果做什麼壞事會到達哪一層的恐怖故事,總是把我嚇的晚上不敢關燈睡覺。
對小時候的我來說,龍虎塔就是兩隻超大的寄居蟹趴在哪裡,只是頭長的不一樣而已,在裡面聽爸爸講故事雖然有趣,但我最愛的還是看著那兩個頭,並且幻想著他們兩人的互動及故事,幻想著老虎其實一直都不開心,因為龍虎塔是龍頭進虎頭出,他覺得很不公平;或是想著半夜他們會爬起來打牌,每次老虎都說贏了就換他當頭等等的有趣故事,當然,有時候為了討好老虎,我也會跟爸爸說今天從老虎開始逛,或許他也會很高興吧?
現在長大了,已經很少去龍虎塔逛逛了,有時會想起當時的自己在那所做的各種蠢事、幻想,還有當時跟爸爸一起逛的各種故事,小時候偶而會聽到膩了小鬧脾氣,現在想想這其實是爸爸對兒子愛與期望的一種表達方式吧?或許下次該找個時間去看看好久不見的兩個好朋友了,當然,也要帶爸爸一起去。


◎文.圖/Momo Jeff
摸摸傑夫,摸摸是狗傑夫才是我,1992年生,目前為接案插畫家,並且正在就讀碩士班,在2014年正式成立插畫專頁以及開始接案,使用水彩淡彩,黑色幽默、大小怪獸,以及使人誤以為作者是女性的各種可愛腳色,都為筆下產物,最大的夢想就是成為一位只用圖就使人感到快樂的繪本插畫家。
FB:https://www.facebook.com/momoandje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