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布日期:2017-07-07更新日期:2017-07-07
【名家專欄】
野生文明
那場群架終究沒有打成。
整理房間時,翻到從前的舊手機。已經是舊到不可考的型號了,也不記得當時為什麼換掉。可能是約滿不續之類的?我反覆把玩著它,注意到手機的上方,磕了幾個彎彎的、淺淺的印子,接近圓形,但又不完全是。不仔細看,會以為都是淺淺的按鈕,又彷彿一排細小、不規則的腳印。
我記得那排印子的來歷。那是一個很好的晴天,典型的南方夏日。我們一群男孩子躲在高中的自習室裡唸書。書本啊教材呀模擬試卷整整齊齊擺在桌上,但人人東倒西歪,誰都心猿意馬的。外面的天氣太好了,好得不像是真的,好得彷彿誘惑而且暗示著:如果沒有什麼事情發生,今天度過的一切,就都不能算數似的。
事實上,整個夏季都是這樣的天氣。金色的、畫面中四處浮動著斑斕躁點的晴天。高中三年的下學期都是如此:該要有事情發生的,但總有更重要的事情攔著我們。有時阻攔我們的,只是憂患之心。隔著透明的窗玻璃,熾熱的青春時光散落一地。但我們坐在圖書館裡,低著頭,讀生物和地科,歷史地理,小心翼翼挖掘著土壤礦藏一般的知識群。
像這樣的時候,一切聲音都被放大了。跟著課本內容,一字一字前進,我彷彿能聽見野牛群涉渡的聲音。
就是那樣的晴天。坐在自習室裡,我和隔壁同學的手機同時震動了起來,旋即靜止。但好像耳朵裡還響著嗡嗡的聲音。眼角餘光看見他似乎伸手拿了手機按著。大概是看訊息。但我沒有。簡訊好好的收在我的手機裡,這是我給自己的約定:做完一件「該做的事」,才能自由去做「想做的事」。但為什麼該做和想做的不是同一件事呢?我需要更多時間去釐清。現在我不讀那則簡訊,好像只要我不去讀它,時間就不會過去。
此刻有更重要的事情。我在看書,雖然心思不在書上,不知道胡亂想著什麼。手機震動起來的時候,我正反覆讀著今日進度的最後一頁,彷彿看見縮得小小的野牛群,正翻山越嶺走過我們的長桌,一個接一個蹬著有力的後腳,攀過我轉筆那手的手腕。胡亂散放的紙堆和試卷在夏夜的風裡輕輕翻掀著,嘩啦啦,發出水一波四濺般的聲音。這是季節交替之間,有什麼就要轉變,而我們提前感覺到了。這是野牛群正在涉渡的季節。
身旁的同學突然譁的站起身來,非常憤怒的樣子。我還搞不清楚發生什麼事,就被他一把揪起身來。圖書館裡大家都抬頭看著我倆,我壓低了聲音說幹嘛啊,他說出事了,那個誰傳了簡訊來,在校門口,走啦,過去幫忙。出事了。
我們跌跌撞撞跑下樓梯。奔到校門口時,人已經散了。不遠處停著警車,閃著燈,但沒鳴警笛。整條夏日午後的長街靜靜的,彷彿已經被消音。我們喘著氣,狼狽看著空無一人的玄關廣場,有點錯愕,很焦急,又有些慶幸。還有更多的情緒,但全攪在一塊一時說不上來。
人呢?我們各自伸手掏著口袋,想找手機,想打電話問人,問什麼都好。但我的手機卻不在口袋中。回過頭去,看見手機落在不遠處路旁洗石子的矮欄邊。我一下子全醒了,慌忙跑去撿起手機。還能開機,面板也沒壞。我一面撥著電話,一邊把手機翻過來轉過去的檢查。完全看不出異樣,除了手機上方,多了一排小小的圓印。
大概是剛剛摔在洗石子圍欄上的痕跡。我聽著手機裡的撥號音,嘟嘟嘟,一邊盯著圍欄看。圍欄是學校前陣子整修花圃時新砌上的,本來土堆就接著柏油路邊,下過雨或風大時難免散漫到路中來。新砌起的矮圍欄像是花圃的城牆。我抬起頭看,看見欄內的花開得與世無爭、妥妥當當的,長長的洗石子矮欄,繞著花圃的邊緣前進,幾乎繞著圍了活動中心一圈,不知道會延伸到什麼地方去?
同學說他們沒事。警察簡直像有預知能力一樣,雙方人還沒烙齊,在球場打球的朋友們離得近先到場,推了幾把,警車就來了。那時我們還在學校深處的圖書館裡和想像世界搏鬥。等我們氣喘吁吁跑到現場時,警車都已經關了警笛,準備要走了。
那場架還沒來得及打起來,青春期就過去了。很多我們想搞清楚、卻終究沒有的事情,好像也就這樣決定了。書本提前告訴我們世界的樣子,但當我們想伸手去指認時,想去改變、去搏鬥時,萬事萬物都已經有自己的名字和秩序。我們只能翻山越嶺的記下這些事情。
找出瞎捲在一起的充電線,勉強抽出線頭和插座,接上電源,重新開機。開機的聲音嘩啦啦響了起來,水花四濺,我好像又看見野牛群的身影,春夏之交的草原上,大河淺灘間,帶著渴望緩慢前行──偶然為了某事激動起來,抵著角,胡亂踩踏,跟著身體裡躁動的熱望和力量,那麼奮力的一起──雖然站在相對的立場,但確實是一起的,鼓足全力,用自己的方式,嘗試打敗對方。

◎林達陽
高雄人。高雄中學畢業,輔大法律學士,
國立東華大學藝術碩士。
在離海不遠的地方長大,喜歡書店、
電影院、室外球場。著迷於旅行、
日常巷弄和能夠看得很遠的地方。
曾獲三大報文學獎、台北文學獎、香港青年文學獎、
教育部文藝創作獎、優秀青年詩人獎等。
詩集:《虛構的海》、《誤點的紙飛機》;
散文:《慢情書》、《恆溫行李》、《再說一個秘密》、《青春瑣事之樹》。
FB:「林達陽」
Instagram:「poemlin0511」
榻榻米與髮油
十歲以前,去得最遠的地方是壽山腳下,外公外婆家就在鐵路局日式宿舍裡。媽媽通常都稱為「去鼓山」。速克達機車噗噗噗前後各載著一個小孩,跨越愛河。那是八十年代,島嶼上日式房舍尚未趕盡殺絕,那一片住有至少二十戶以上的寧靜區域,小紅門,黑屋瓦,圍牆覆滿絨毛似的老苔。
去的時候總是周末或寒暑假,其他表弟表妹也常來,因此,日式房屋在我記憶裡總是與慢悠悠的假日時光相連。不苟言笑、闊額大眼的外公,白汗衫灰短褲,蹲在後院裡修剪盆栽,替植物換土,清理魚池,橘色水管長長地曼放在盆栽與盆栽之間的狹窄走道,幾個噴壺散落,外公不愛我們這時候去打擾他,我都是隔著客廳綠紗窗、影影綽綽地望著他,低矮天花板吊著一隻風乾了的河豚標本,鼓腹凸眼,隨著外公站起身來的嘿喲聲,和一點點流水般的風,在我們頭頂轉呀轉。
至於外婆,瞇著本就細長的眼睛,連身花衣服,一般是芋灰蛋黃之類色彩,永遠在廚房轉著,照看孫子們愛吃的一鍋滷肉,不然就盤坐客廳隔壁的榻榻米上,縫補衣服或做什麼小手工。母親去了,大多與外婆促膝在榻榻米上低聲說話。我從不知道她們說些什麼。母親與外婆說話全部是閩南語,與我說話就會轉換為台灣國語。榻榻米區其實不是個房間,是客廳、廚房、外公房間之間的過渡地帶,榻榻米又平坦又結實,俯面嗅聞還散發一股特殊草味,一直是小孩子們最喜歡流連之處。我當時在做些什麼呢,多半是輾轉在她們旁邊讀書,書是從成家以後就搬出去的小舅舅房間裡找出來的,可能是昆蟲圖鑑,或世界書局版用紙輕薄的《小五義》,或《讀者文摘》。偶然她們的聲音會有一二句因為激憤而高聲起來,但是我也老不記得內容,不知是數落各自的丈夫,或交換不肖親戚近況?
回外婆家,都是外婆替我洗澡。我非常喜歡和外婆在浴室度過的時光,熱氣蒸騰裡,我站著,她坐在一張長久為濕氣浸潤而顏色變深的木凳子上,雙手極有勁道地替我擦洗身體。還記得青春期剛剛開始,是小學四、五年級,我仍要求外婆幫我洗澡,媽媽舅舅們全都取笑,說大人大種,還要阿嬤幫洗身軀?那時候,我才回味過來,身體產生變化了,身體是自己的了,邊界要收得嚴密些。
或者,外婆也會從小壁櫃裡拿出白色高高的瓶子,倒出一湯匙什麼,叫我一口氣喝下去,喝下去以後會反胃很長時間,像是身體的隔間裡刷了油漆,氣味揮發,久久不散--是鈣乳--後來讀到張愛玲〈紅玫瑰與白玫瑰〉裡寫王嬌蕊也喝了這玩意,然後說:「喝牆似的。」佟振保笑了,說王太太說話真有勁道。我也笑,想這寫法真厲害,喝牆,那比刷油漆要傳神得多。
覷著外公不在,小孩子們,包括我,會溜進房子最底端的,專屬外公的房間。那裏頭瀰漫一種陌異氣息,說不上來,不是立刻就讓人貪婪深呼吸的香氣,也並不討厭,很濃厚,有黏性。當我們玩笑似地拿起外公在高雄火車站工作用的神氣深藍色硬身大盤帽,想往對方頭上戴,那氣息加重了。啊,就是髮油,工作日的清晨,外公隨身以玳瑁小扁梳仔細梳得服貼,光可鑑人,再將大盤帽鄭重戴上。

◎楊佳嫻
台灣大學中文所博士,清華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著有詩集《屏息的文明》、《你的聲音充滿時間》、
《少女維特》、《金烏》,
散文集《海風野火花》、《雲和》、《瑪德蓮》。
在鹽埕路上

回憶大學時期,只有要去旗津才會經過鹽埕,再到哈瑪星搭船過海。一個偶然機會系上在駁二藝術特區辦了公仔展覽,我身為專案成員,幾乎每個禮拜都從學校搭車到鹽埕,也因為喜歡的女生在鹽埕工作,理所當然勤奮得來找她。
鹽埕對當時的年輕人而言是陌生的,不過沉靜的街區因為辦了展覽而開始有了大排長龍的人潮,也因為當時的活動,創造了現在特區內工人及漁婦的公仔符碼,周邊的公園路和大五金街,彷彿和這工人及漁婦符碼相連結。後來的工作也一直和展覽周邊活動有關。展期結束後跑去當兵,回來剛好是大五金街全面拆除,也和追了好幾年的女孩分開,時代的符碼同時被清除了。
有時候在想,一個產業、一條街甚至一棟建築,都和人們的記憶相關。過去常和同事們去大五金街小巷弄吃的汕頭意麵,後來也不知道搬去哪裡了。現在,騎著單車在鹽埕路上穿梭,都會感受每天有一些改變,新開的店、新來的人潮,或是哪間店又消失了。被刪除的畫面如果不去回憶,不會深刻感受到改變。我們選擇性的記憶所好,以及海風吹過來的生命之味,像是在告訴人們要把握當下,如同鐵件的鏽蝕,象徵著時間的痕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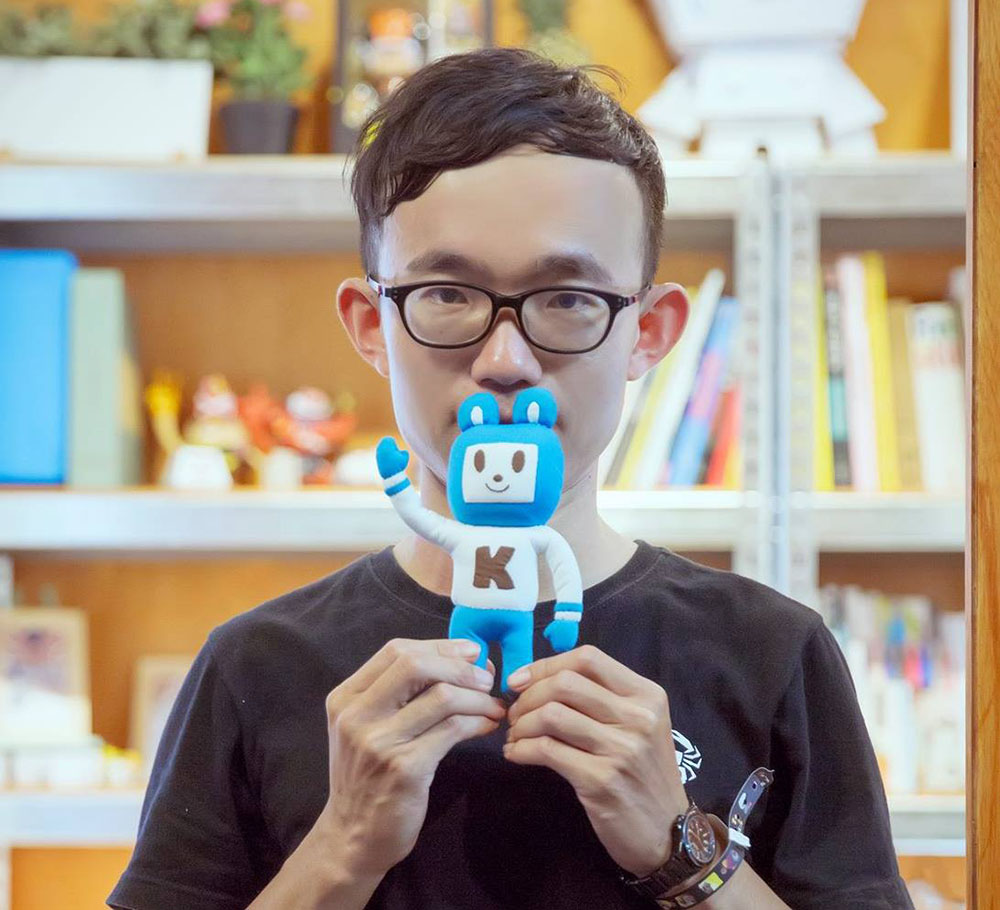
◎文.圖/Macaca
熱愛高雄的南投人,創作卡榫紙玩具和插畫,
創作角色「濱線熊」傳遞高雄文化。
曾與昇恆昌合作高雄機場站慶、高雄郵局郵票與郵筒、
君鴻國際酒店紙玩具禮品等,透過插畫展現高雄的美。
FB:https://www.facebook.com/hamahoshi